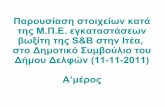Phys 446 Solid State Physics Lecture 11 Nov 29 (Ch 11)(Ch. 11)
敦煌研究院第五代掌门赵声良: 从“伤心学问”到“传播中国...
Transcript of 敦煌研究院第五代掌门赵声良: 从“伤心学问”到“传播中国...

112019年11月5日 星期二 责编:周劼 美编:陈昌 版式:丽菲 责校:洪洵
读 周刊
诺贝尔文学奖什么都没有说 专栏视觉革命与《双子杀手》 读书扫一扫发现更多主编 刘敏
【访谈】
故事
老祖母坐在火炉旁,讲着年轻时的故事。炉火渐渐熄灭,话语也逐渐沉默,只剩下一堆片断与灰烬。你说那故事是年轻还是年老?不知道。惟有记忆在时间的两端跳跃。“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讲完故事,老祖母会这样感慨,就如同一个童话里程式化的结尾。
了解敦煌从故事开始,听着樊锦诗讲着常书鸿、段文杰的故事,再听着赵声良讲着樊锦诗的故事,
“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敦煌便在几代人薪火相传中活了起来,年轻了起来。
敦煌学,无论文献中的历史语言学也罢,壁画雕塑中的美术史也罢,是显学,也是专家之学,不是我们芸芸凡俗者所能懂的,我们了解敦煌,是从故事里听来的,是来听故事的。远一点,飞天、九色鹿——敦煌文物里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多种语言文字的故事;近一点,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罗振玉、张大千的故事;再近一点,几十年敦煌坚守者的故
事;更近一点,巡山大王乐乐狗的故事……就像王世襄把自己的著述集成取名叫《锦灰堆》,既是历经磨难后的劫灰,也是老去故事里的炉灰。
好的博物馆应该是有故事的,好的历史遗迹应该是讲故事的,如同拜伦在《哀希腊》中说:“慷慨兮歌英雄,缠绵兮叙幽欢。享盛名于万代兮,独岑寂于斯土。”他是在对着一堆石头和荒土的废墟追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我们面对敦煌百窟千佛,也当作如是观,哀也罢,喜也罢,每一页文献,每一幅壁画,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片段,就像我们行在异地,听当地人用方言交谈,有一搭没一搭,听懂的是只言片语,但如果有故事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故事里包含的情感、心思和我们没什么不同,那么我们便能从陌生的语言里读出深沉的脉络。
两个异乡人听懂彼此的故事就是朋友,同样,历史的两端,有故事连着,就是奇妙的生命之缘。
文/周劼
敦煌研究院第五代掌门赵声良:
从“伤心学问”到“传播中国声音”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苍茫大漠中,“敦煌的儿女们”留下了青春、才华、岁月,前赴后继。其中代表人物——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
诗,不久前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也再次让全社会关注到这群莫高窟“面壁人”。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接受了读+专访。今年,他的新著《敦煌旧事》一书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书
中主角,正是那些为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默默奉献终生的人们。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已是历史
赵声良在莫高窟图书馆
敦煌:古丝绸之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莫高窟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
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 735 个,壁画 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 2415 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南枕祁连山,北靠北塞山,东临三危山,西接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敦煌寓意
“盛大、辉煌”,它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的说法。有史料为证,公元 964 年(宋代)的酒账单,记载了当地政府的公务用酒,包括数量和用途,如宴请、接待使节、犒赏等,账单共100条,反映了当时敦煌繁荣的文化和多民族的密切交往。
季羡林先生曾评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1987 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9 年,由敦煌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摄制了大型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以亚洲文明对话为题材,向人们展现了不同文明之间命运相通、文化相通、艺术相通的奇妙关联。
敦煌的儿女们在敦煌藏经洞陈列馆的石碑上,有著名学者陈寅恪
的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这个一眼千年的伤心地,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
中国的敦煌研究事业终于发展起来。在《敦煌旧事》中,赵声良将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
1944 年 1 月 1 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自此,莫高窟结束了无人管理的状态。创办之初,常书鸿率领职工白手起家,调查洞窟内容,临摹壁画。但沙漠之中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一年之后,大部分工作人员先后回到内地,常书鸿坚持要把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的事业继续下去,工作人员没有了,他再次四处招聘人才。1946年至1947年,受常书鸿感召,段文杰、孙儒僴、欧阳琳、史苇湘等陆续来到敦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一辈子都献身敦煌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
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到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研究人员也陆续增加。
作为第三代,樊锦诗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敦煌,她和同仁把考古学应用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中来。20世纪90年代,当她继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她清楚地看到了敦煌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敦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成了她的奋斗目标。
樊锦诗说:“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才问题。如果没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在这里,敦煌的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赵声良回忆,21世纪初的某一年,国家文物局统计全国文物系统高级研究人员信息,发现全国文物系统有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仅十多人,其中敦煌研究院就占了一半,“博士当然不能说明必然层次就高,但在敦煌这样边远的地方,能聚集如此多的人才,也算是奇迹了。”
赵声良的苦与乐第四代院长王旭东今年接任单霁翔,已经成为新任
故宫博物院院长。赵声良则是第五代。20 世纪 80 年代,赵声良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带着几多向往,他奔赴敦煌。
赵声良还记得他初到敦煌时的房间,土墙、土地,还有一个壁橱,地上是扫不完的尘土,天花板是用废报纸糊住的,还露出几个黑洞。有一次晚上睡觉,一只老鼠不小心从黑洞那里掉下来,正好掉在了赵声良的枕头边,又顺势沿着被子里面的缝隙向里钻,从赵声良的脚边出去。到了冬天,作为南方人的赵声良掌握不好火炉的封火技术,常常半夜火就熄灭了,夜间温度零下十七八,又冷又困,早上起来,鼻孔旁边都是冰碴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敦煌艺术的魅力。”赵声良说,“如果没有这样迷人的艺术,我恐怕也不一定能坚持在这里。过去段文杰先生说他当年在敦煌时是‘一画入眼
底,万事离心中’,不管生活有多么艰苦都不在乎。我也有同感,我是研究美术史的,敦煌壁画彩塑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敦煌艺术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世人所了解,我在研究、挖掘敦煌艺术的价值,就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从壁画中的山水画、故事画、飞天等方面都作过研究,每一项研究都有很多新发现、新收获,因为都是前人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知道的内容。每一篇文章的发表都很有成就感。”
而今,敦煌研究院有一千多名职工,专业研究方面包括保护研究、考古研究、美术研究、文献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人员,相关的还有信息中心(图书馆)、期刊编辑部等机构。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洞窟管理、安全保卫以及洞窟讲解人员,以及一批行政、后勤人员,“我们的研究人员包括文科和理工科等多种学科,他们都在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在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等领域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窟霸乐乐大王谁能想到,如今能在莫高窟“称王称霸”的,是一只
名叫乐乐的小土狗。2018 年 4 月 4 日,莫高窟官方微博发布一则通知,
称窟区降雨夹雪致栈道积水严重,暂停开放,随文附一张浑身是泥、白毛已然滚成褐毛的狗狗照片,曰:“窟霸乐乐大王早起巡山已回,路况可见图片”。这萌狗惨状,不知怎的就戳中了网友趣点,一时转发无数,引来权威媒体争相报道,乐乐大火。自此,去莫高窟跟乐乐合影,成了一种时髦。莫高窟也紧随热点,为乐乐绘制漫画讲述敦煌故事,让它成了名副其实的“代言狗”。
在窟霸狗之前,莫高窟还有一位风靡的代言动物是九色鹿。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作品《九色鹿》,以敦煌壁画《鹿王本生》为灵感创作,为莫高窟第257窟中的九色鹿赋予新生。
年轻一代用自己的方式走近莫高窟,古老的莫高窟也借助现代科技拥抱这个时代。现在,每一位到莫高窟的游客,都会看到卧于沙漠之中的现代化建筑——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在进入洞窟之前,人们可
以在这里观赏高清数字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等,了解莫高窟自然、历史、文化背景和数字化洞窟景观。为保障洞窟壁画和彩塑保存环境稳定,敦煌研究院采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构建了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可以实时监测气象、空气质量和颗粒物,当 洞 窟 内 的 相 对 湿 度 超 过 62% ,二 氧 化 碳 超 过1500ppm(1.5‰)的预警指标时,工作人员可以暂时关闭相关洞窟。
“数字敦煌是用新科技保护和传播敦煌艺术的重要方面。”然而,赵声良并不认为新技术、新传播能真正使敦煌变得“年轻”,“敦煌经历了一千多年已经很衰老。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返老还童’,我们要做的是特别小心地保护敦煌壁画,尽最大的可能延缓它的寿命,让子孙后代能看到,而不是在我们这一代使它毁坏。数字敦煌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把敦煌壁画全部、真实地保存下来。那样,即使遇不可抗拒的因素而毁坏了,也可以通过贮存的数据来复原它。”
利用新的科技来保护敦煌文物
读+: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掌门,继承前四代的衣钵,您面临着怎样的局面,将做哪些工作?
赵声良:我面临的局面是在几十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基础上,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敦煌研究院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在文物的科学保护、学术研究和文化弘扬方面形成了较好的规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是在前人开拓的道路上行进。但是在新时代仍然面临着很多新问题,特别是当前的文化建设,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方面。我们将努力在敦煌文化保护研究与传承方面努力奋进,特别是利用新的科技来保护敦煌文物,同时加大传播弘扬敦煌文化的力度。另外,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敦煌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读+:如果梳理 1944 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的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您如何总结?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已有75年的历史,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保护、研究和文化弘扬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从最初的看守状态发展到今天的科技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发展为预防性保护。我们有一支过得硬的保护研究队伍,在文物科技保护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4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科技部和甘肃省委省政府依托敦煌研究院先后成立了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先后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30 多项。其中 10 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不仅有力地保障了敦煌石窟的文物安全,而且推广应用于全国 11 个省(自治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效提升了我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技术水平,推动了整个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
其次,在学术研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所有洞的时代、内容的考证。完成了多个系列的研究专题,出版了大型学术系列著作《敦煌石窟全集》(共26卷)。并在石窟考古报告的撰写,石窟美术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在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与民族宗教研究方面形成了本院研究的特色和优势。
从1981年开始创办的院刊《敦煌研究》至今已出版175期,现在已成为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是国际敦煌学界的必备参考。
不论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学术研究,都伴随着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发展,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敦煌事业的长足发展。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得到发展,我们也同样推动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国际敦煌学的发展。
最后,传承弘扬方面,在保护好的前提下搞好莫高窟旅游开放。以新的保护与利用理念进行旅游开放的管理,通过游客承载量的调查,确定洞窟每天的游客承载量,在这个基础上有效地控制参观人数。为了解决保护文物和开放利用的尖锐矛盾,建立了数字展示中心,使游客对敦煌艺术获得更好的欣赏和全新的视觉体验,达到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也形成了莫高窟特有的参观体验新模式。
此外,我们让敦煌艺术走出敦煌石窟,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敦煌艺术展览,所到之处,无不在当地引起轰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同时在数字敦煌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新媒体虚拟洞窟的形式,把敦煌艺术经典之作传播到世界各地。
敦煌文物包含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多种语言的信息
读+:《敦煌旧事》回顾了您扎根敦煌 30 余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您见证了中国敦煌学由弱到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说法今天是否已经完全推翻?
赵声良:“敦煌学”是指以敦煌石窟、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文物以及敦煌周边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由于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内容浩如烟海,敦煌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古代的历史、宗教、民族、艺术、科技等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敦煌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可是,敦煌学一开始就是一门
“伤心的学问”,由于大量文物流失,我国自己的学者反而要到外国去调查这些本来属于中国的文物。更令人伤感的是,经历了10年浩劫,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于国外,以至于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这个说法已经成为历史,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在敦煌学研究上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我们也不能自满。还应该学习国外好的经验和做法,还应该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就是要有开阔的胸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团结国内外的学者共同研究敦煌学。
读+:为什么海外同样热衷敦煌学研究?赵声良:一个客观原因,由于上个世纪初敦煌藏经
洞出土的文物大量流失国外,主要存于英国(1 万多件)、法国(6000 多件)、俄国(1 万多件)以及日本、美国等,大量的古代文物引起了欧美及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有相当多的学者投入到研究工作中来,因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敦煌学。
另一方面,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敦煌文物包含着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多种语言文字等十分广泛的内容,是了解中国和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因而受到海外学者的重视。
读+: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赵声良: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敦煌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已经有一些工作在开展,与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等国家都已经有一些交流,比如阿富汗希望共同研究保护巴米扬石窟壁画,今年与柬埔寨在吴哥窟保护方面达成一些合作意向。未来,敦煌研究院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机构,可以为国家承担一些大国责任,在国际社会的文物保护弘扬方面努力工作,特别在应用现代科技进行科学保护和开发应用方面。